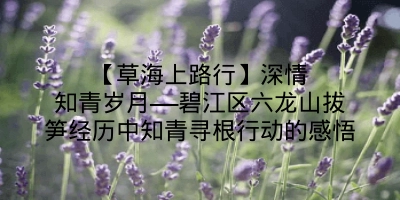和你差不多一样大的时候,我们就离开学校,告别家乡。
去农村,到兵团,垦大漠,戍边疆!“奔赴祖国最艰苦的地方!”然而,一旦现实野携和理想砰然对撞,我们才发现脚下的路是那么的漫长。
天苍苍,野茫茫,日晒雨淋田里忙;稻田里,坡头上,汗流浃背湿衣裳;窝窝头,玉米棒,没到日落饿得慌;油灯暗,炕头凉,多少回梦里喊爹娘。
知青岁月里,有人觉醒,有人迷茫,有人失落,有人逃离,有人坚强。
更多的人在无奈中年复一年地等待,等待花开,等待希望!这就是,当年我们的青春。
嗨!姑娘,别光叫我“奶奶”,我,另有一个名字叫孙拿“知青”。
在你和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们就下田插秧,种高粱,割小麦,采果子,收庄稼忙!脸,晒黑了;手,割破了;累了,饿了,太阳怎么就不下山了?小王瘦了,小李病了,小张哭了,我想妈妈了!夜,总是那么长,城里的玫瑰花,已开得怎么样?大街上,流行什么花衣裳?同桌的那个“他”,如今,又漂泊在何方?南飞的大雁啊,何时能带我回故乡颂凯伏!天亮了,梦醒了,脸上的泪,还在不停地淌。
那就是,我们的真实少女时代,太多的回忆,定格在当年的模样上。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知青”。
经过十年的磨练,十年的渴望,我终于又重新回到了课堂。
灵与肉的历练 ——忆我的知青生活 (原创)
三.汗滴禾土洗铅华(下)
秋收
金秋时节,金穗满园,稻谷飘香。放眼田野,泛 红的高梁宛如窈窕淑女亭亭玉立;黄澄澄的谷穗压弯了腰枝,微风吹过掀起层层谷浪;丰腴的苞米撑破了绿衣,披散着一袭粽色的秀发。大自然毫不吝啬的把累累果实赐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节气告诉人们该开镰收秋了。其实,最先开镰的当属盛夏时期割麦子。大约是下乡头一年,我们几位男知青手握镰刀干了把真正意义上的农活儿。来到麦田,极目望远,满目金黄,那丰收的图景着实招人喜欢,惹人爱。但此时它却不愿与你亲近,当你把他齐根斩断的那一刻,它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刁难你,戏弄你,以报复你的无情。不信?我后面的”悲情”故事足以印证了这一点。接下来,打头儿的一声令下,几十人的割麦大军一字排开,刷刷的割麦声格外清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与麦子拼争,不知是刀钝,还是手拙,抑或是麦子过于强悍,不大的功夫,累的我是腰酸背疼腿发软,两只手蜷伸受阻不灵活。环顾左右,我已与割麦大军渐行渐远,看来“付班长”的位置非我莫属。再往后望,人家留的麦茬又短又齐,反观鄙人的“大作”,麦茬明显高出一截且高高低低,自己见了都心烦。老打头的巡视过来直叭嗒嘴,心里话:这是咋整的,咋割成这个熊样?我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不敢直做誉视这位老农,倒不是胆怯,而是羞愧与内疚令我无地自容。唉,不管怎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于是,我打起精神,继续往前拱。
(上为本组男知青田间照,崔孟勋提供。)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汗液从每个毛孔里涌出,滴进眼里辣辣的,流进嘴里咸咸的。裸露的胳膊和面额被锋利的麦芒扎满印痕,痛痒难挨。天气灼热,咽喉冒烟,赶紧喊来送水的社员,咕嘟咕嘟一通凉水下肚,顿觉清爽。我自小肠胃不好,以往对生冷食物从不敢造次。但眼下补水是人体第一需求,不然就有笑闹虚脱的危险。至于肠胃能否接受这“不速之客”,也无暇顾及许多了。稍加喘息,我留意了一下隐隐作痛的手,这才发现握镰的右手布满水泡,抓麦子的左手中指不知何时与镰刀亲近,划破的伤口还在流血。我连忙从兜里掏出准备擦汗用的手绢,当作纱布缠在手上。处理完毕,我俯身割麦时,看到脚下的那一幕,不禁哑然失笑。只见右脚上的农田鞋顶部划出一道嘴般大的口子,本该封闭的地界儿已门洞大开。没错,又是镰刀头子惹的祸。你别看它割麦子愚钝,可要割起人来那叫兵不血刃。幸运的是“邪(鞋)不压正”却能护主,如果刀尖再往里进一点儿,那可怜的“五兄弟”就该破相了。没曾想,初试牛刀竟如此狼狈不堪。其实,来到农村,广阔天地就是考场,每一项农活儿都是知青们无法回避的课题,需要醮满心血和汗水加以解答。唯有付出才有收获,唯有付出才会铺就成功之路,所谓自然法则中的因果关系就在于此。想到这些,我心释然,待秋季收谷子时,手中的镰刀似是轻便了不少。谷子是起垄播种,每人抱四根垄,先从中间两根割起,割一段距离往回割一侧单垄,到头再割另一侧垄,边割边打腰捆成捆。如此往复,循序渐进。长长的垄,长长的天,弯弯的镰刀,弯弯的腰。庄稼人付出的是艰辛,收获的是希望。你看,人们手捧沉甸甸的谷穗,笑意挂上眉梢,喜悦滋润心田,丰收让我和农民兄弟们陶醉了!
(上为本组男知青田间照,崔孟勋提供。)
(上图为同班女知青田间照,李松梅提供。)
打下来的谷物等运到场院,沿周边码成 垛 ,打场时拆垛破捆平摊在场院中间,马拉着石碾子在上面转圈碾压。有意思的是,马的双眼用布蒙着,问社员此为何意?社员笑答:如果马睁着眼看到满地粮草,还不让它糟踏个够?这牲口光顾吃了还能好好干活吗?不过,你别担心它看不见道,它走的可好嘞,不信你瞧……盲马沿谷物一圈圈转着,不偏不离,马步平稳有序,看来老马识途之说果然不虚。
碾压一段时间就要翻动一次谷物,如此往复直至谷子全部脱落后拿掉谷草,将谷子传成堆,开始扬场。几个人站在上风头,用木锨铲谷子使劲抛向空中,杂物随风飘去,谷子堕落地上。看似简单的动作,我却好一阵子未参透个中门道,抛出去的谷子散落不开,其间的杂物怎么也厘不清。后经老农指点才渐渐领悟。一锨上去,该飘的尽飘,该落的完落,对我而言,纯升段飘去的是无知的烦忧,落下的是成功的欣慰。
谷子边打边装袋归仓。生产队除留够谷种外,其余的做为口粮往各家各户送。下乡数载,诸如栽秧挑水,挖菜窖、挖防空洞挑土筐,跟车拉脚当装卸工等这些苦大力的活儿,总少不了我和孟勋,赶上为社员家送粮,我俩自然是不二人选。虽说送粮少有挑水、挑土筐那么紧张,但200斤的粮袋子一旦压在肩背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屯子里多为坡道,每走一步全凭一口元气顶着,稍有松驰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所幸的是爹妈给了我一付看上去很骨干却还算硬朗的身板儿,又经农村风霜雨雪的磨砺,重负之下未压倒,一路坎坷却坚挺。如今古稀之年仍腰腿无羕,这岂不是天养人乎?
(上图为本组男知青田间照,崔孟勋提供。)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农民们祖祖辈辈劳作于天地间,汗洒于田野上,图的就是全家人有粮充饥,有衣遮体。对农民而言,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辛苦了一年,人依旧,粮食却没了。这绝非危言耸听,我们队就曾发生过这种疟心的事。那年秋季的一天,风干气燥。场院里谷物等堆积如山。望着就要到手的粮食,忙忙碌碌的社员们累并快乐着。可就在这天的下午,场院北侧粮垛的后面有一股浓烟冒出,烟借风势越冒越大并伴有火光显现。这时只听有人撕心裂肺的大喊:不好了,粮垛着火了!话音刚落,但见火光冲天而起,直烧得粮垛劈啪乱响,眨眼间便连成一片火海。社员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火情惊呆了,等回过神来想要救火时,因场院在屯子外,周边没有水源,更没有当今的各类灭火器材,人们眼睁睁的看着熊熊烈火吞噬着命根子却无力回天。待跚跚来迟的消防车赶到现场,北面的粮垛已损失殆尽。面对遍地狼藉的场景,社员们的绝望与哀怨溢于言表,老书记瘫坐在地,老泪横流。是啊,在那个食不裹腹的清贫年代,半年的口粮被付之一炬,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
后经调查,此次火灾是几个农家娃躲在粮垛后面点火柴引起的。真是造孽啊!队里德高望重的潘义林大爷其孙子是玩火者之一。事发后,老人家很长一段时间呆在家里代孙闭门思过,整日以泪洗面,无颜见父老乡亲。正当人们忧心重重之即,从区政府到公社、大队都给予我们政策上的扶持和口粮上的补贴,帮助社员们度过难关。正所谓大火无情人有情,雪中送炭济苍生。这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但队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屋里热热的,人心暖暖的。
大灾过后,生活依旧。全队上下铆足了劲耕耘新希望,播种新梦想。有人说火烧旺运,此话虽有些调侃的味道,但有时也往往会灵光乍现。这不,第二年我们队粮菜丰收,社员收入看涨,老老少少皆大欢喜。我暗自思量:人生无常,世事难料,福与祸,幸与不幸尽在冥冥之中轮回。只要我们身处顺境不张扬,身陷逆境不折腰,随遇而安,勇敢面对,就会与幸运牵手,与幸福相拥。你说对不?
收获的季节收获的不仅仅是果实……
冬储
秋去冬来,满眼的金黄渐渐褪去,东北大地恢复了黝黑的本色。冬天是备耕与休整期,其中,积肥是备耕的重中之重。生产队自筹的农家肥少之又少,远不能满足种植需求,因此,每年初冬队里都要组织社员到市里淘粪。1973年11月,我和崔孟勋自告奋勇加入淘粪队伍。那一刻我不禁想起一段往事:那是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举办文艺汇演,我们班排练的节目是小歌舞《我是快乐的淘粪工》,我扮演在前面拉粪车的小车手。记得歌中唱道“小粪车我的好朋友/天天拉着你到处走/我在前啊你在后/天天拉着你到处走/拐弯向前看,注意保安全……”那优美的旋律,欢快的舞蹈,至今仍记忆犹新。但谁能料到,十年后的今天我居然把少儿时代的小歌舞移植到广阔的农村大舞台上来,扮演了一回真实版的淘粪工角色,生活与我开了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玩笑。然而,我已不再是当初那个稚气未脱的少年郎,农村的历练使我能够理性的面对现实。现实是,那年的冬天知青点只有我和孟勋苦苦坚守,如果说室外的冷是冷在肌肤,那么蜷缩在冰点以下宿舍里的冷则冷彻心髓。哥俩儿每天肌寒交迫,度日如年。而到市里淘粪,生产队管吃又管住,饭菜热乎乎,挣着高工分,还能逛马路。如此美差,求之不得。至于苦累脏险、颜面缺失之类在温饱面前大可忽略不记。
此次淘粪一行10人,租住哈市某中学(孟勋说是哈尔滨第四中学。)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子,搭一上下通铺和炉灶,余下的空间几乎容不下10人同时站立,进屋就得脱鞋上铺。每天清晨,除一人专职做饭外,其他人则棉服压身,腰系麻绳,肩挑粪桶,直奔厕所。哈市与天津的公厕主体结构别无二致,区别在于哈市公厕一改多个粪坑的模式,改为约一人多高,男女厕所连通的化粪池。这一改,男女本该私密的声响在这里你想不听都难。粪池里的排泄物基本不冻,淘粪时,用扁担钩勾住桶梁,从蹲板上的排泄孔放入池中,再用扁担头或木棍使劲往下摁桶,装满后前手作支点后手压扁担,一桶尿粪混合物便提上来了。有过多年淘粪经历的社员文姬余(年初重返哈尔滨时,该人已故去,写此文权作纪念亡灵吧)为我们做示范,他经验老道,整套动作干净利落,令人称道。就要与往日躲都躲不及的人体排泄物零距离接触了,本就五味杂陈的心头又凭添了一种别样的滋味。不过,此念一出,稍纵即逝。历尽磨难的知青饱尝人间五味,再多一种滋味又有何妨?于是我接过了粪桶。开始的的过程挺顺当,往上提时,感觉桶很沉,扁担直晃悠。好不容易提到蹲板孔,手一颤动桶端碰到蹲板上,因用力过猛,直撞得“粪花”飞溅,这下可好,没等我直起腰来,飞溅的那个“花”撒着欢的往身上脸上“亲昵”。哎哟哟,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赶忙用袖口发力的擦拭,“花”是没了,可那脑人的味道却如影随形。有一种尴尬叫啼笑皆非,对,这就是我当时的心境。唉,淘粪的活儿都干到这份儿上了,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
池子里的粪便所剩无几,粪桶已不能直接提取,这时就需有人从蹲板孔下池子清理。这活儿非瘦小枯干的青年社员周恒坤莫属。小周虽年岁不大,却有几年的“淘龄”了,因长的小巧玲珑,所以下池子几乎成了他的专利。小周脚穿雨靴站在池子里用铁锹一锹一锹往桶里装粪。化粪池有长度没宽度,身体触壁的事时有发生。按说淘厕所不能影响人们方便,有些人进来见此情形扭头就走,另谋他处。可赶上内急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个窝就是一通霹雳啪啦来个痛快,哪还顾得上下面有人。这下可苦了小周了,他赶紧躲到一边以防污物灌顶。令人不解是,等他上来非但毫无沮丧之意,反倒是一脸诡异的笑模样。他借题发挥,调侃历次淘粪蹲在池中抬头仰望那一刻的糗事、孬事,说到兴处眉飞色舞,淘淘不绝,仿佛他看到的“西洋景”比他闻到的“满口香”还要有滋有味。面对这位农民小兄弟,我有些茫然:最美的年华,从事着天底下最埋汰的工作,这家伙竟能够在谈笑风声中化污浊于无形,化忧烦为快乐,我禁不住为他的超然与洒脱而赞叹。
每淘一处公厕就在附近找一块空地,用土围成圈,挑出来的粪便倒在圈里,东北天冷,一宿的功夫便冻住了,第二天队里早早派人装车拉走,以免影响市容和有碍人们出行。除了淘公厕,也稍带淘周边居民大院里的小厕所。和农村一样,院里的厕所用木板钉成,男女共用,是名副其实的公共厕所。蹲板下方挖一蓄便坑,由于常期堆积,冻层下方的粪便已发酵变黑,用锹挖时,一股雾状的气体伴着恶臭扑面而来。七十年代的农村本无劳动保护可言,社员们又怎舍得自掏腰包买口罩戴?几年的农村生活我和孟勋名为知青,实为农民,因此,即使是有口罩,在与社员境遇趋同的情况下,又怎好意思遮住脸面呢?只得忍着吧!可一个“忍”字换来的是鼻子呛的发酸,眼睛呛的流泪,嗓子呛的咳嗽,第六感官饱受难以名状之苦。中午收工回到驻地,本想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可眼前的一幕又让人眉头紧锁:房间太小,打水洗脸得排队,有的哥们儿干脆连脸都不洗,好歹涮涮手抄起碗筷就吃饭。白天尚且好过,到了晚上这一大家子人都挤在铺上,尽管脱掉了外衣,但早已被大粪味渗透的棉袄棉裤却不离左右。长长的夜小小的屋,紧闭的门户不透风,每一次呼吸就是一次感官的折磨。何为臭气熏天?在这里会给你最精准的答案。头几个夜晚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可几位农民兄弟则早已鼾声大作进入梦境。敢情那首《今夜无人入睡》不是唱给他们听的,这或许就是适者生存的法则使然吧。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渐渐的适应了这个环境,融入了这个集体,活儿干的欢,饭吃的香,觉睡的实,已然成为地地道道的淘粪工。
(上图为市内淘粪合影照,崔孟勋提供。)
历时一个多月的市内淘粪结束了,临行前哥几个刻意梳洗打扮一番走进照相馆。正如孟勋所言,我们身上那挥之不去的气味令拍照人员颇有微词。尽管如此,还是拍了一张平顺三队淘粪工“全家福”,连同那段难忘的心灵洗礼,一并珍藏于心。
时间定格在1973年12月15日……